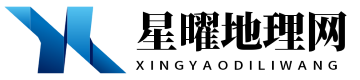编者按:黄秉伟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名誉所长,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 他还是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美国地理学会会员、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荣誉通讯会员、国际山地学会顾问。 1996年获国际地理联合会特别荣誉奖,1997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进步奖。其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了纪念黄先生对我国地理学作出的杰出贡献,特邀请黄先生的首届研究生牛文元教授撰写本文。
小时候粗略地读过《五六先生传》。 我时常向往那种“寡言少语,不求荣利”,甚至“不愁穷,不迷财”的人,默默地向往。 成为人生的榜样。 长大后,我有幸在黄秉伟教授手下任职。 三十多年来,我深深地受到他的学识、风度、道德、文章的影响,心中一直崇拜的影子也逐渐栩栩如生,变得更加清晰,越来越突出。
黄秉伟先生,1913年2月1日出生于广东惠州。 20世纪20年代是中华民族的屈辱时代。 军阀混战,列强入侵,民生日益衰败,山河危亡。 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男孩,聪明、早熟,充满正义感。 他稚嫩的心过早地承受了沉重的压力,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广东是清末民初革命的发源地,各种思想聚集。 惠州毗邻香港。 廖仲恺、邓演达、叶挺等国家精英在这里出生和成长。 他们与广大民众一起,奏响了那个时代的强音。 8岁的他虽然不谙世事,但依然懂得“责任感”这个沉重的词。 在学校里,他听老师念“华夏皇帝即将沦为奴隶,国家日新月异”。 他忍不住泪流满面,无法自抑。 再过一会儿,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和“打败军阀、消灭列强”的豪歌,让他十分激动。 尽管已经过去了近70年,但每次回忆起往事,他依然记忆犹新。 好像是一样的。
黄秉伟先生12岁之前就进入私塾,吸收了很多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特别是在叔叔家受到的熏陶,影响了他的一生。 其叔父早年追随康有为,主张维新变法。 1898年维新运动彻底失败,他隐居家乡,热爱家乡的山水。 他在临泉长大,自食其力。 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他痛恨社会的黑暗,不愿让世界沉沦。 他经常教侄子读很多正气著作,以表达自己“不为太子,而行高尚之事”和“忘却得失,自尽一生”的情怀。 这些文化的交融不免对黄秉伟的世界观产生了重大影响。 半个多世纪后,黄先生总结此事时,深有感触地写道:“隐居者的思想,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内容,对于那些沉迷于名利的人来说,是一剂良药。”对于为祖国和人类服务的功利主义者来说,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为了祖国和人类,有时我们可能不得不效仿伊尹,以治而进,以乱而进……隐士思想的影响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对我60多年的地理经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工作也有很大的影响。”
黄秉伟先生自幼以孝心、手足之情闻名乡里。 由于家里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他深感温饱不足的担忧。 当他即将选择职业时,虽然知道在外资控制的机构(如邮电局、海关等)工作可以找到高薪的“铁饭碗”,但他毅然放弃了做一个渣男的工作。 财富在外国人的羽翼下。 当时,他从报刊上了解到,各种外国人正在中国进行探险活动,深入西北、西南腹地。 然而,能够参加这些探险活动的中国人却屈指可数。 这种排外为主的现象,在爱国主义时代得到了体现。 他心里觉得这实在是国家的耻辱。 他在《自传》(1992)中说:“乃新希夺冠,速度快,奔放,两年内连跳五级,考入中山大学预科理科。 ” 然后,他必须决定是学习化学还是学习地理,这是一项终身学习。 在他的决定中,虽然他还无法理解现代地理学的内涵,但他觉得中华民族的子孙无法对祖国的美丽山河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他不假思索地就踏入了地理学的大门。犹豫。 作为各科优秀的学生,他毅然与地理结下了不解之缘,既有奉献者的情怀,也有战士的悲剧。 只有当个人的不公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时,往往才会有持久的生命。 他自17岁在中山大学专心学习地理以来,一直致力于这一领域,直到去世前一天。
中国的近代地理学起步并不早。 中山大学地理系是系统教授西方地理学思想的先行基地之一。 1929年,中大地理系聘请来自“现代地理学之乡”德国的Wilhelm Klettner教授担任系主任。 随后,Wilfgang Biansha教授被聘为系主任。 同时,他还邀请了当时国际地学界的其他几位著名教授,彻底移植了西方地理学体系。 众所周知,德国是现代地理学的发源地。 洪堡、里特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大师让许多地理学史上的研究者惊叹不已,称赞他们“就像科学史上巍峨的高山”。 。 黄秉伟先生在这个体系中从事科学地理学的研究,一下子走进了当代地理学的前沿,扎根在中华博大的沃土上。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科学地理学既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也是一门难度很高的学科。 一不小心,要么掉进一堆琐事,要么掉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迷茫境地。 普通平庸之人在鄙视、蔑视地理的时候还能如此“酷”,实属罕见。 因此,能够真正理解地理真谛的人并不多。 而往往需要一生甚至几代人的时间,经历“迷茫——清醒,迷茫——清醒”的多重曲折,才能体会到它的内涵和外延,体会到凤凰涅槃般的惊喜:原来地理是一个如此丰富多彩的世界。
在中山大学地理系,他认真听讲,如饥似渴地读书,深思熟虑地探索,逐渐认识到:要了解地理规律,必须依靠地理事实的发现、地理事实的比较。内容和地理知识。 进行实验需要积累地理学各个分支的知识; 还需要借鉴相邻学科的成功经验。 不了解地理的综合性,就像做饭没有米饭一样。 在校期间,他选修或旁听了许多地质学和生物学课程,并涉足矿物学、古生物学和动物学。 由于对德国教授的一些观点存有疑虑,他自学了一门简单的高级课程。 数学; 他从研究气候学的角度思考了地理定位实验研究的重要性; 他偏爱地貌学,延伸到掌握地球结构、内生力和土壤科学的知识; 他学习人文地理学,对聚落地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人口统计和人类影响有了清晰的了解。 为了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他特别注重实地考察。 当时,中大地理系每两周举行一次实地考察。 黄秉伟先生身体非常虚弱。 他第一次去白云山是随德国教授Kreltner。 还没走多远,他就已经筋疲力尽,脸色发青。 他必须休息。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继续。 然而他却是临危受命,从此他无一例外地进行了所有的野外实习。 经过一年的磨练,他“已能临危不惧,绝非后人”。 正是通过严格的智力训练和体能训练,他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不仅拓宽了自己的知识结构,而且练就了强健的体魄,为他后来从事地理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自己说:“在四年的学习中,我了解到地理和自然地理学是需要建造的大厦。它们刚刚开始建造,材料还不齐全。云在坠落,星星在坠落。”跌倒了,还需要努力。”
其毕业论文《惠州西湖与潼湖地形图》调查细致、推理透彻、分析精准、结论扎实,得到卞沙教授的高度评价,满分97分。 他的四年总成绩名列全校第一。 。 获得学校的学术卓越金质奖章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
地理区域的综合识别、地理结构的客观排列、地理空间的分异规律、地理过程的振荡节奏一直是地理学追求的基本目标。 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地理国家,位于地球上最大的陆地欧亚大陆东侧、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西侧。 它恰好夹在地球“两大活动区”之间。 ”,自然环境非常复杂,正确认识我国的地理特征和区域分异特征并不容易。需要扎实的地理学理论基础、详尽而有条理的资料、准确的方法和缜密的思维,需要具备分析问题的能力。渗透多个研究领域,黄秉伟先生与生俱来的天赋和勤奋的努力使他能够胜任这一艰巨的任务,无论是在学校学习,还是在社会工作,他都不断背负着这个艰难的“十字架”,不断前行。
1934年,黄秉伟先生因中山大学理学院应届毕业生中学习成绩最好,在何彦轩教授、卞沙教授的推荐下进入北平地质调查所。 德国著名学者李希霍芬访问中国后,曾确定中国南部海岸为下沉型,北部海岸为上升型,并为中外科学家所相信。 年轻的黄秉伟根据自己的调查和多方比较,向这个世界级的权威提出了挑战,认为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我国地学奠基人之一翁文浩先生鼓励青年科学家到山东进行沿海地貌考察。 于是他两次前往山东,对荣成附近的北镇、日照沿海的几处平行沙洲、芝罘岛的穿山小峡进行了严格的观察和记录。 最后他得出结论,山东海岸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沉。 第一份检验报告出来时,发表在中山大学《自然科学季刊》上。 洪思齐教授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书评,多加赞扬。 他对中国学者对重大问题的见解深感自豪。
黄秉伟先生思路清晰,逻辑明显。 其字如椽,言辞宏大。 他认为自己不太擅长辞藻,自认为“用笔说话”。 世界上所有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无论你多么能言善辩,如果没有真才实学,没有实际知识,就只能试图去奉承别人,最终只能空腹。 虽然黄先生承认自己口才不是很好,但由于他讲的内容实用,说理真诚,听者还是受益匪浅。 在一次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上,与格里普讨论华北海岸时,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引起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丁文江先生的认可。 作为当时地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丁先生由翁文浩和曾世英合编的划时代的中国地图集出版不久。 他正准备编一本长版的中国地理,并据此写了一篇简介。 高中中国地理。 听完黄秉伟在会上的发言后,我请黄总第二天参加工作。 这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文化项目。 众所周知,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可用的地理数据不仅非常少,而且详细程度也相差甚远。 它们在地域和时间上的口径不同,很难比较。 黄秉伟知道任务艰巨,但他毫不畏惧。 他欣然答应,并于1935年秋来到南京,开始了另一段曲折的旅程。 当时他只有22岁。
编纂中国地理的第一步,就是对南陵进行认真考察。 在我国,传统观点是将南岭视为“地理界限明确”,有“岭上梅花开,南枝暖北枝冷”等诗句为证。 。 在国内外各种地理著作中,也被代代相传,视为理所当然。 按照当时的认识,中国北半部的地理界限比较明确,基本没有争议; 南半部的问题更多。 丁文江先生指出南岭问题是最重要的,他要求黄秉伟就地解决。 对待工作一向认真的黄秉伟,用了近半年时间走遍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省份,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 他发现仅从地貌来判断并不足以得到问题的答案。 他必须综合考虑气候、土壤、植被等自然因素,才能综合判断一个地理区域的性质。 最终的结论是:南岭只是一条水线,不是山脉,不应该作为自然地理边界。 就这样,他从实际考察出发,走上了综合分析中国地理特征的道路。
专着《中国地理》(丁文江先生称“长版”)仅完成三分之二,正值抗日战争兴起。 书籍被打包,办公室被搬迁,现场工作变得不可能。 “长期”的写作工作被迫辍学,高中时只完成了一封关于我国地理的信。 一些保存下来的手稿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 虽然屡次暴露在军火之下,但泛黄的纸上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 在那份手稿中,引用了大量的内容,内容极其丰富。 理论、数据、结构、策划,甚至用词造句都非常讲究。 以1936年在南京编写的《中国植物地理学纲要》为例。 全书共136页,35000余字。 它讨论了中国的植物区系组成、人类活动和天然植物、中国的植物区和国内植物。 让我们从这四个基本部分开始讨论。 在充分考虑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将中国划分为26个植物区并一一解释。 读来我仍然深深感受到它的学术价值。 本书特别讨论了人类对自然植被的干扰和破坏。 书中写道:“每逢战乱,官邸、住宅都难免遭到破坏;乱局过后,流民逐渐返回故乡,聚会日渐繁盛。如果政府建造房屋来满足需要” ;如果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建设项目来维护环轮的美丽,将需要更多的木材……导致以前的森林变成荒山。” 由于本卷分析的针对性,张启云先生曾将植物纳入其中。 区划部分发表在《历史地理杂志》上,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黄秉伟先生在编纂中国地理时,一直把正确划分中国自然地理区域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之一,而这绝非一蹴而就的。 黄先生早在学生时代就养成了博览群书的习惯,具有可贵的开拓进取的学习精神。 以这种进取精神为经线,以学科间的有机联系为纬线,编织了他对地理学认识的基本网络,充满了他勤奋追求和进取精神的特点。 纵观他的研究工作,综合观点、比较方法、因果联系、现实意义、应用价值等一系列现代地理学内涵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书山有路,勤奋是路,学海无边,船是船”。 “”是黄先生最喜欢的座右铭,充分展现了他在学术道路上的勤奋、刻苦、毅力和毅力。 大学初期,他偏爱地貌学,写的第一篇论文是《广东西湖与潼湖之间的地貌》; 大学三年级时,他对气候学产生了兴趣。 此后,他受到了韦斯的影响。 在曼的影响下,他系统地研究了植物地理学。 到了1936年,他觉得当时的地理界对土壤科学还不是很熟悉,于是他向土壤地理学家索坡等中国同行请教。 他还参加了土壤调查,广泛阅读了国外出版的有关新疆、内蒙古、东北地区的资料。 土壤数据,重新编制了全国土壤图,不仅填补了原地质调查院土壤研究室编制的中国土壤图的空白(该图不包括上述列出的省份和地区),而且还改进了讨论的内容和使用的方法。 它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注重土壤与其他自然因素之间的联系。 正是这种广泛的探索和深入的研究,使他逐渐发现了中国自然地理区域形成和结构的真正含义,为他研究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奠定了基础。
1984年10月黄秉伟先生访问日本时发表重要讲话:“地理学家都明白,不同尺度的划分是认识‘土地’的一种手段。按照认识的顺序,首先要进行自然划分。” ” 这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他非常重视地理划分的研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类研究会贯穿他半个多世纪的科学活动。 他在《中国地理》手稿中,对全国范围内的各种自然要素进行了系统的划分,这对于客观认识中国的地理特征无疑是一大贡献。 先后完成了“中国河流划分”、“中国气候划分”、“中国地貌划分”、“中国土壤划分”、“中国植被划分”、“中国综合自然划分”等。 上述划分,有些是他首次提出的,有些是前人提出的,但他是从综合的角度重新划定的。 以《中国气候区划》为例。 竺可桢、涂昌旺先生最初提出,但他们只考虑了单一因素,特别是地貌、植被、土壤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将云贵划分为一个单元。 针对这一点,黄秉伟先生在《中国气候区划》一文中做了一些重大修改,将原来的云贵地区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 他的见解不仅受到当时人们的关注,也得到了气候区划原作者的高度赞赏。 涂昌旺先生极力主张将其论文公开,并发表在浙江大学历史地理教育研究室刊物上。 一家人的意见对于科学的发展是相互印证的。 科学家们的务实精神和学术交流态度一时成为传奇。
1930年代左右,黄秉伟先生正确描绘了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的雏形,明确将青藏高原划分为一个大区域。 这与1957年至1959年间组织的大规模自然区划项目不同,做法不同,效果相同。 1949年后,在竺可桢、黄秉伟的领导下,聘请了一批苏联专家为顾问,对中国自然区划进行了全面研究。 担任中国区总顾问的萨莫伊洛夫教授在区划原则和方法方面介绍了一些好的经验和想法,但他对中国自然地理特征的认识远不如中国学者深刻。 提出具体建议是没有道理的。 黄秉伟先生根据多年的实践,以充分的论据推翻了萨莫伊洛夫教授长期以来的观点。
由于黄丙伟先生对中国自然区划研究的巨大贡献和中国自然地理区划的重大国际影响,罗马尼亚科学院于1964年授予他名誉通讯院士称号,以表彰他在中国自然区划方面所做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地理。 这些成就包括他对黄河中游水土流失的研究、对我国第一部自然地图集的贡献、对我国实验地理学的倡导、对现代地理学研究新方向的探索、对农业生产潜力。 对研究的追求,他设计和领导我国第一个热湿平衡研究,他为我国地理事业发展所做的组织工作等等。
1990年,在《地理知识》出版40周年之际,他用流利的草书写下两句深刻的话语:“倚枕看旧游记,藏书余味于胸。” ” 这个以书为友、以书为伴、以书为食的忠诚长辈,几十年来一直在书的海洋里徜徉。 享受三摩地、享受三摩地的人,除非亲身经历过,否则无法理解。 人们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为了国家、民族、人类。 从小到晚,他始终将这种正直和思想融入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中。
作为一名科学家,黄秉伟先生历来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任命他为地理研究所所长。 在此岗位上,他明确提出了三大任务:一是黄河中游山区与陕西之间的峡谷水土流失研究。 他把黄河中上游和下游联系起来,他把水土保持和治理黄河联系起来,他把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联系起来,他把黄河安全联系起来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可见其高瞻远瞩。 2、南方山区利用。 他知道中国人口的压力,他知道土地资源的珍贵,他知道山地利用的潜力,当然他也知道一个科学家的责任。 3、工厂选址。 这里是地理学家应用空间分异理论服务国民经济建设的好地方。 从更一般的推论分析,也是他“科学救国”的合理延续。 上述三项任务涉及环境、农业、工业等各个方面。 经过40多年的考验,可见他们非常有远见。 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地理学深入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
我劝你不要刻顽固的石头,但路上路人的嘴就像纪念碑。 黄秉伟先生的事业和性格是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了解的。 八十多年来漫长的岁月里,他的生活近乎枯燥,但他的世界却异常丰富多彩; 他的要求很少,但他的贡献却无法用一卡车来衡量。 他所说的远远少于他所做的。 说了这么多,但他的形象已经不需要人们多说什么了。 他精神很好,继续走路。 没有人会相信他已经80岁了。 他没有直接告诉我他对地理学未来发展的看法,但我暗想也许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达:“地理学一直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它研究自然而不研究社会” “无自然基础的经济”,即继续运用地理学理论更好地服务国计民生。也许他能总结出他的答案!
简历和传记
1913年2月1日出生于广东惠阳(今惠州市)。
1928年秋考入中山大学预科,1930年升入中山大学本科。 193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学术卓越金质奖章。
1934年至1935年,获得洛克菲勒文教基金会奖学金,到北京地质调查所研究山东沿海。 他提出了海岸沉降的证据,并修正了冯·里希特霍芬关于中国长江以北海岸具有上升性质的论点。 。
1935年至1938年,应丁文江先生、翁文浩先生邀请,在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编着《中国地理》(长版)和《高中中国地理》。
1938年至1942年,任浙江大学历史地理系讲师、副教授。
1942年至1949年,历任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专员、专委、技术干事、研究委员。 承担和主持我国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规划水库调查、长江三峡、黄河下游多目标流域规划等任务。
1949年至1953年,任南京生产建设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工业部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华东财政经济部工矿普查组主任兼基建处副处长。 1950年夏兼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室副主任。 1953年调入地理研究所,历任研究员、代所长、所长、名誉所长。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院士)。
Since 1950, he has served as deputy director of the Natural Zoning Working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Atlas Compilation Committe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Chinese Physical Geography” and other positions. He also served as the vice chairman (1956-1979), chairman (1980-1991) and honorary chairman (1991-) of the Chinese Geographical Society for a long time, and served as the editor of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64-1984) and the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1982-1992) Chief Editor.
In 1964, he was awarded the title of Honorary Corresponding Member of the Romanian Academy of Sciences (later changed to Academician). He was elected as a member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in 1979, was awarded an honorary corresponding member of the Royal Society in 1980, and was hired as a consultant to the International Mountain Society in 1980.
Huang Bingwei is a member of the 3rd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3rd, 5th and 6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a member of the 5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odern geography in China, Huang Bingwei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rends and tren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the discipline itself, advocated crossover and penetration between disciplines, emphasize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ctively introduced new ideas,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methods, and paid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emphasizes serving economic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racticing it.
Since the 1950s, Huang Bingwei has continuously pioneered and guided many comprehensive research works in physical geography, such as natural zoning in China, soil erosion and conserv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water conservancy and agriculture in North China, improving sustainable productivity of slope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c Research. His main contributions can be summarized as:
Huang Bingwei’s research on China’s natural zoning began in the late 1930s. The “Floral Regions of China” and “Climate Regions of China” published in the 1940s were of pioneering significance in China’s early sectoral zoning.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ural Zoning (First Draft)” edited in 1959 is China’s most detailed and systematic monograph on national natural zoning. There has been no similar work at home and abroad so far. China’s natural environment is extremely complex.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ny factors, it is objectively difficult to identify zonal patterns. Huang Bingwei’s monograph exposed and affirmed the ubiquity of zonal patterns, which was a huge historical breakthrough for the study of natural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s in China. In the 1960s and 1980s, he simplified and revised the original plan to make it easier to apply, emphasiz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regional units as a whole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ir close integration with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won the second prize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Award in 1987. This achievement has been widely used by agriculture, forestry, water, animal husbandry, military and other departments for decades.
As early as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50s, Huang Bingwei proposed the direction of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surface physical processes, chemical processes and biological processes. This is about 20 years earlier than developed countries conducting similar research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Later, it was proposed that experimental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soil-plant-atmosphere system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and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farmland natural production potential” were proposed and developed. Huang Bingwei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and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ysical geography and influenced several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physical geography.
Huang Bingwei first complet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soil erosion pattern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in 1953, and compiled China’s first 1:4 million soil erosion zoning map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se works are still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Loess Plateau. Huang Bingwei’s zoning plan and instructions are still used in relevant plans prepared by the water conservancy department, lay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management planning of China’s soil erosion law research.
Huang Bingwei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uti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lopes in eastern China, pointing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prevent soil erosion and deterioration of soil physical properties, but also to prevent the supply of soil nutrients from being reduced; strategic improv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slopes should be based on plant measures to maximize the improvement of one side of the slope. Or the best way to achieve sustainable productivity in a small watershed is to rely on fast-growing plants to eliminate damage and bring benefits, which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util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slope land.
As a pioneer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 research, Huang Bingwei advocates repeated use of bottomup and topdown methods to observe climate change according to natural divisions, conduct research on dangerous area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tudy China’s agricultural, forestry, and animal husbandry practices. Active countermeasures and measures that should be taken in the industry and energy utilization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global warming. He pointed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geography to study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uitable for China’s conditions, with 50 years as the main target time, so as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earth system science. In the earth system, we should focus on the land system and its extension with the atmosphere and ocean, and integrat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nto one furnace. These opinions have become the focus and work guide of recent research.
To sum up, Academician Huang Bingwei has pioneered and guided many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physical geography in my country since the 1950s,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promoted geography in my country, especially physical geography research, an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Many research results are still important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water, and military departments.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duction practice, show great vitality, and have far-reaching influence at home and abroad. Huang Bingwei is a great master of geography in my cou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