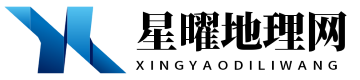近几十年来,西方(主要是英语国家)出现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文化研究热潮,被称为“文化转向”。 有评论称,这一发展可视为“二战”以来社会政治观点的深刻变化。 各个社会学科都将“文化”置于研究焦点,开创了社会正义、归属感、认同、价值等问题研究的新局面。 在文化转向的社会科学潮流中,人文地理学家也十分活跃,文化地理学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成为最具时代精神的地理学分支之一。

英国地理学家约翰斯顿在其著名的当代地理学评论著作《地理与地理学家》第五版中,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称为“文化转向”,并明确列为一章。 最近出版的西方文化地理学领军人物邓肯等人主编的《文化地理学伴侣》(2004)中有两章专门研究“文化转向”。 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思潮为理论基础,主要以所谓“新文化地理学”的兴起为代表。
一般认为,英国地理学家杰克逊和科斯格罗夫是新文化地理学的先驱,提出要关注文化的内部运作、符号产生和价值内涵,然后根据这些内容来审视空间。 构成、空间秩序、空间竞争的“文化转向”,使原本颇具人文色彩的西方地理学更加深入地探究社会人文本源。
由于社会和人文的繁荣,社会问题日益超过自然环境问题,人类社会本身的危机浮现在思想家和学者面前。 早在十八世纪,马尔萨斯就认为社会问题可能比自然问题更为紧迫。 1871 年德国的统一令地理学家拉策尔兴奋不已。 他将注意力从学术研究转向德国的人文现实,研究德国人的生活方式。 拉策尔前往世界各地进行视察。 十一年后,他出版了《人文地理学》第一卷,九年后出版了《人文地理学》第二卷。 虽然拉策尔将“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中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但拉策尔的研究在西方人文地理学中尚属首创。 一百多年来,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得到了强劲发展。
20世纪上半叶,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地理学家卡尔·绍尔的影响下,他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点引入人文地理学研究中。 在措辞上,扫罗也喜欢使用人类学家常用的“area”一词,而当时的地理学家大多使用“region”。 索尔后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任教多年。 在他的领导下,具有浓厚文化历史特色的“伯克利学派”逐渐形成。 一般来说,西方成熟的文化地理学始于美国的伯克利学派(而20世纪后期的“新文化地理学”也是作为对伯克利学派的挑战而出现的)。 地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携手,拓展视野,更新视角,吸收相关理论,不断丰富自身内容。 这是西方人文地理学得以持续深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只要看看约翰斯顿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柴彦伟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你就会发现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概念阵容相当广泛,其中有许多重要的社会科学内容。概念 基本概念和前沿概念可供人文地理学研究参考。
伯克利学派采用的文化概念是基于对环境决定论的否定(扫罗批评的对象是他的老师森普尔女士和通俗学者亨廷顿的观点),并借鉴了人类学家的“超有机”概念。 文化概念将文化(而不是自然环境)视为控制人类行为的重要力量,是一种稳定力量。 从文化、环境与人的关系来看,文化是动力,人是行动者,环境是改造的对象。 文化的存在先于人们的行动。 这是伯克利学派研究的前提。 这种文化概念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的文化理解方式。 英文单词culture(文化),其拉丁语原义是“培养”、“培育”。 人有了文化,就得到了养育和教育。 因此,早期人类学家所表达的文化概念往往带有“超有机体”的味道,如:“文化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原则和自己的规律。几个世纪以来,它拥抱着每一代人的僵化。天生的成员,并将他们塑造成成年人,为他们提供信仰、行为模式、情感和态度。” (怀特)在这种文化观念中,有很强的文化决定论。
以给定的文化为参照,或者说提取文化特征为第一步,然后考察人——按照文化原则行动的人——如何改变自然景观并创造相应的文化景观,是伯克利文化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套路学校。 受早期人类学的影响,扫罗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主要是非欧洲文化地区,重点关注农村地区,较少关注城市。 索尔的学生逐渐关注“美国文化”,对美国本土文化景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他们的综合成果以《美国文化地理学》一书为代表。 本书作者威尔伯·泽林斯基(索尔的学生)明确表示,他采用了“超有机体”文化的概念,并刻画了超有机体“美国文化”的特征: 1.强烈的、近乎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2. 2. 将动态和变化视为最高价值; 3、机械主义世界观; 4.完美主义和救世主。 泽林斯基重点关注这些方面,分析了美国文化景观的特点。
1920年代至1950年代时期是美国伯克利文化地理学院的鼎盛时期,影响很大。 索尔本人当选为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 在回顾现代西方地理学发展的著作中,总是有大量对伯克利学派(英国地理学文献中也称绍尔学派)的评论。 在20世纪初的地理学界,对这门学科本质的认识仍然不明确。 但扫罗主张以文化景观为研究对象,明确确立了地理学的人文方向。
然而,对于中国地理界来说,扫罗的名字似乎只是最近十几二十年才被人们所熟知。 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中国学者虽然努力引进西方现代地理学理论,但似乎对扫罗学派并没有太多关注。 在近代编撰的许多中国地理文献中,很少见到索尔的名字。 这种情况可能有两个原因。 20世纪初,国家积贫积弱。 中国地理学家一是救国救民的心,二是相信科学精神。 因此,他们更加注重救国救民的“生命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科学描述山川大地的自然地理学。 扫罗的文化研究远没有环境决定论那样“科学”地令人震惊。 另一个原因是当前文化地理学的发展高潮提升了扫罗学派的历史地位。 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索尔学派虽然在美国享有盛誉,但在地理学界可能并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显赫。
伯克利学派使用的“超有机体”文化概念预设了覆盖整个社会的主导文化力量的存在。 这种文化力量是给定的、统一的、稳定的。 对于这种文化,即主流文化,学者们可以准确地再现表征。 “超有机体”的文化概念并不是扫罗的创造,而只是传统的延续。 这一传统文化观念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受到猛烈的批判。 在话语、文本、解构等新思潮的背景下,超越人自身而存在的“超有机体”文化概念当然被抛弃了。 此外,对于文化景观的理解也出现了新的视角。 风景不再是客观的自由场景,而是必须主观“阅读”的“文本”。 象征意义、文本误读、再创造等种种问题随之而来。 来。 新文化地理学给人的初步印象主要集中在阐明这些问题上。
随着文化转向的深入,新文化地理学的关注范围开始加大,主要体现在对“社会空间”不公正的批判上。 对文化概念的新认识是扩大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围的理论基础。 对于文化的概念,新学者抛弃了“生活方式”等松散的描述,直指文化内涵的焦点——价值观和相关的象征意义。 地理学家科斯格罗夫说:“人文地理学当前的文化转向引入了新的隐喻和类比,这些隐喻和类比更符合对意义而非功能的强调。” 学者进一步指出,社会中的价值观是多样的、冲突的、不断演变的。 我们应该关注和同情长期被忽视的“他者”的文化价值观,为他们遭受“主流”文化的歧视和压迫寻求正义。
各种后现代思潮推动了对“传统”观念的挑战,所谓传统观念在西方社会日益盛行。 如果说洪堡和利特尔通过考察非西方世界开创了现代地理学,那么后现代地理学则通过研究西方社会本身而出现。 西方社会的弊病,特别是美国社会的弊病,成为激进学者攻击的对象。 在深挖政治、经济、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时,价值观的潜在影响、价值观的压制和冲突几乎随处可见。 西方社会的花园里,原来也到处都是荆棘。
以西方(美国)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社会空间的分布格局(如女性空间、同性恋空间、无家可归者空间等)中,许多歧视、压抑、排斥、不公正的情况显而易见或隐现。 )空间等),这些都是新文化地理学在“文化转向”中所关注的主题。 以社会空间替代自然空间(甚至完全放弃自然空间)是新文化地理学研究主题的一大特征。 随着文化观念的变化,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不仅仅是文化人的地理,而且还研究具有各种价值属性的各种社会群体的社会空间。 正因为如此,文化地理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许多研究都有交叉。 由于以“价值”为核心的新文化概念的广泛运用,各学科纷纷将各种社会群体的价值表达纳入研究视野,文化转向已成为一种趋势。
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的空间形式,同其时间形式一样,都是一种基本形式。 特定的空间形式总是对应着特定的价值、符号和意义。 因此,文化地理学用独特的空间思维来揭示价值的空间形态,讨论象征意义的空间表征。 在人文社会研究中,地理学的地位再次受到尊重。 在“文化转向”的同时,社会学和政治学也出现了“空间转向”,社会空间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所谓“社会空间”并不是指一个客观的、抽象的、可以“填充”各种社会内容的几何空间。 社会空间总是具体的,是特定社会事物的存在形式。 任何对社会空间的“填充”,实际上都是“侵入”和“竞争”。 社会空间不可能是静态的存在。 社会的任何发展冲击都会导致社会空间的变异和空间话语的更新。
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变革。 面对这个时代,英国文化学者大卫·钱尼表示:“文化及一系列相关概念不仅是核心话题,也是能够促使我们重新认识当代社会生活的最有效的学术资源。” “如何理解现代性、现代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后现代性,成为文化转向的触发因素以及文化转向中反复遇到的问题。” 对现代社会社会空间的文化解读自然成为新文化地理学家领域的积极举措。
女性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扩张也体现在文化地理学中。 甚至有人认为,女性主义地理学家(不一定都是女性)是推动新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群体。 社会空间中女性空间与男性空间的“竞争”得到充分探讨。 大社会是男性空间的世界,家庭是男性空间压迫女性空间的地方。 这些房屋是为“标准”家庭设计的,妇女和残疾人不是主要考虑因素。 女性在家里是无酬劳动者,而男性则是在家中的享乐者。 家对男人和女人来说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城内的雕像都是男性英雄,象征着男性的成就。 商场的主题就是诱惑女性消费。 所谓的“公共空间”实际上是男性空间,根本不考虑女性的安全感。 天黑后,这里就是年轻人的世界。
家可以是与外界对抗的基地,可以是家庭暴力的巢穴,可以是男人失意时的避难所。 但“家”却是“无家可归者”所无法企及的空间。 在美国社会,“无家可归者”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 他们逐渐在街角、公园里创造出自己的空间。 伯克利大学校园外不远处,有一片草地,布满了“无家可归者”营地。 这是一个著名的“另类”空间。
唐人街是移民的代表空间。 尽管中国社会学家提醒人们“中国不是一个只开餐馆的国家”,但中餐馆仍然是唐人街的象征。 无论经过多少代人,生活在唐人街的华裔仍然摆脱不了“移民”和“另类”的社会定位。 正是这个“社会空间”让中国人翻身无门。 中国人想要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就必须离开这个空间、这个地方。 但他必须在全新的、完全美国化的社会(所谓美国主流社会)中“挤”出“上流中国人”和“美国式中国人”的空间,这并不容易。 鉴于他的身份,他的文化空间永远是一个问题。 在归属和选择之间,存在着痛苦。
美国黑人群体、女性群体,甚至同性恋群体、无家可归者群体都在努力展示自己的文化,争取自己的社会空间,而一些中国人却想掩盖自己的文化,消解自己的社会空间。 这种不同的走向反映了不同的历史经历和不同的价值观。 有些中国人认为“可耻”、“低等”的事情,黑人和同性恋者并不认为。
文化学者注意到,当今社会(不仅仅是西方社会),有一种正在快速发展、空间迅速扩张的文化形态,这就是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的迅速扩张扰乱了原有的文化秩序。 精英文化不再是社会文化的主宰,大众文化开始主宰社会。 边缘文化、底层文化(如嘻哈、方言小品)融入流行文化并占据空间,成为景观中的突出部分。 进入这样的氛围,知识分子虽然变得更加自由,但却失去了对社会的影响力。 大量文化形态转化为产业,成为消费资源。 我们新的不仅是“知识经济”,而且是“文化经济”。
一些学术知识是流行文化的重要资源。 地理知识一直以来都是贴近大众的,现在更是涉足流行文化、时尚文化,受到市场的欢迎。 美国的国家地理、加拿大的加拿大地理、英国的地理都有很好的市场效益。 中国的《中国国家地理》和《中国人文地理》也是如此。 历史学、考古学的部分知识内容也转移到了大众文化中,但它们的话语权根本不在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手中。
流行文化具有占据社会空间的自然倾向。 在大众文化占据的广阔空间中,很难找到精英文化的符号。 城市空间和媒体空间是广告话语的世界,广告话语依赖于大众文化。 承认一个地方就是接受一个意义框架。 在充满电影、电视、报纸和广告的空间里,观众(无论其真实身份如何)总是被定位为“消费者”,因为流行文化的消费大于其审美价值。 在这样的社会空间中,文化精英首先感受到了文化危机。
文化精英,其实不仅仅是文化精英。 既然大众文化已经获得了空间霸权,就需要对空间进行重构或重组,以证明其自身的价值。 住宅装修是最基本的空间重构和符号设计。 在流行文化的压力下,各个社会群体正在构建不同类型的空间场所来展示这个群体的重要价值观和关系结构。 社会空间重构的推动力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文化。 主动的人善于整合环境中的资源,而被动的人在社会动荡中只是环境的奴隶。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如何与流行文化竞争,保证自身的社会空间,提升自身的价值,是社会空间再分配的重要问题。 郊区一直是一个被精英阶层看不起的地方,但现在它可能是一个文化保护区。“郊区是一种出于道德考虑的居住形式,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一个相当现代的地方。” (钱尼)。
社会贵族(出身的、精神的、政治的)抵抗流行文化的方式就是创造自己的空间和场所,尤其是区别于“大众”,抢占社会空间的“头等舱”。 刻意为社会贵族打造头等舱的做法,正是流行文化流行框架的产物。 文化框架不仅提供意义,还提供词汇。 今天的“贵族”已经失去了词汇,社会贵族的空间也不复存在。 旅游文化是一种完整的大众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大众地域文化。 它融合了各种神圣典雅的文化空间(皇家宫殿、贵族庭院、教堂寺庙、高等院校)和地方特色空间(古村落、古城镇)。 、自然风光)全部转化为大众旅游文化空间。
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冲击,深刻影响着当今的生活。 文化转向确实是由文化危机引发的。 “空间就是金钱”,但与金钱并行的还有“空间就是文化”。 社会地理学家哈维表示,当今的社会空间正在被压缩,高密度的社会空间令人窒息。 私人空间、群体空间、公共空间、功能空间(包括环境空间)之间的竞争正在改变社会空间的整体格局。 我们必须面对这种文化空间的转变。 如果我们不想成为空间环境的奴隶,我们就必须清醒、勇敢。 这就是新文化地理学提醒我们的。
发表于《读书》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