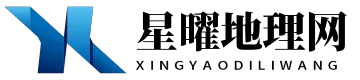湘西大山里的天气喜怒无常,早上还春阴漠漠,冷得让人发抖。还未到中午,阳光便穿透了云层,恰比河峡谷被炙烤得“滋滋”作响,烟雾蒸腾,像极了仙境。去补点有两条线路,从吉首市驱车,沿峒河和恰比河交汇的地方出发,一路溪流潺潺,草色染绿,花卉怒放,这是去补点最近的线路,约莫十来分钟便可抵达目的地;组团采风,关在旅游大巴的车厢里,亦可直取209国道,从斜插云端的矮寨大桥下绕道X077旅游公路,沿途皆是雄山秀水和星罗棋布的苗寨,因为有景致可看,倒让人忘了时间的蹉跎。 有人说想娘的时候,就摸摸肚脐,那曾是和她血脉相连的地方。在补点,村庄是补点人的娘,这是在补点生活了五十年的原住民、当了二十多年村支书的石天银脱口而出的话。他的话耐听,初听像诗,再读是书,充满哲理和乡愁。他打着比方,如果大山是娘的头颅,恰比河恰如一条弯弯绕绕的脐带,一头牵着村庄,一头流向远方。想家了,去河流经过的地方,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因为没有滋生太多对生活的敷衍和算计,藏匿在湘西岩溶奇观深处的补点村依旧保持着苗寨朴实的风貌和烟火色,因此成了吉首人周末游山玩水的好所在。 我去过三次补点,第一次是两个人,第二次是一个人,第三次是一群人。每一次去补点,脑海总会冒出“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的句子,美丽而忧伤,这样的情绪就像大太阳底下的树荫,有些凉快却令人郁郁寡欢。可又无法“不如见一面”的纠结,停停走走,趁着春天去恰比河右岸的水井、丛林和村庄,去那个无拘无束的自由滩涂,给孤独放生。 溯恰比河而上,逗留最多的地方是补点附近几个苗寨被废弃的碾坊。因为长时间无人问津,昔年碾米的闹热场景不再,碾槽两旁长满了野树荒草,这些前人用过的石器,大浪淘沙般被抛弃、被遗忘,却又无时不刻印证着历史的变迁,令人唏嘘。 对补点走心,完全是因为“补点卡”,“补点卡”是补点村的一个自然寨,意即“我家的客人”,这也是石天银随口道来极富想象的译意。这种语言的延伸似乎遵从了翻译“信达雅”三原则,让补点卡看起来有些抽象却又有更富具体的洒脱和浪漫。而我一直不甚明白,“补点卡”是指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游人是“我家的客人”,还是这个村庄本身就是恰比河的“客人”? 大约两者应该兼而有之。 村庄,是人的载体;人,才是村庄灵魂。 在三百年前或者更早的时间节点,补点人的先祖就在恰比河右岸生了根,开始赓续一座老村的历史文脉。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何而来,或者是逃荒、打猎以及避难,他们总是要勇敢地去深山老林带来的凄风苦雨。 补点不大,百来户人口的村庄,镶嵌在大山的脚背上,就像溪谷拱出来的一个小小扇贝,在中国地图上,甚至可以直接被忽略。但当踏上寨门口的青石板路,却又总会被那里的一草一木所感动。 从逼窄的巷道望去,补点仿佛又是恢弘巨制的原始雕砌,那些包浆了的刷了一层又一层厚厚油漆的民居,人影幢幢、光可鉴人。令人惊讶的是,房子虽然上了年纪,俱是屋挨着屋、檐挨着檐顺着山势往上建筑,中间也有斑驳的封火墙隔离开,鳞次栉比,整齐地如同卫兵。村寨不大,依山傍水,却是好看得不得了。令人感动的是,每一个去补点的游人,迎面遇见背柴大娘、采茶阿婆还有健步如飞的苗家汉子,他们通常热情地打着招呼“来了呵”,然后斜开半拉身子让对方先通过。 这种礼让是一种风骨,镌刻在村庄的深处,代代传承。 村口的右侧是一片阔叶林,郁郁苍苍,以枫树为主,生长得十分茂密。一阵风吹来,甚至可以听得见叶子和空气摩擦出的“哗哗”作响的气流声。 在寨子左前方,挺立着一颗巨大的树,大约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不知其名,树冠散开,像一把伞。当地人介绍,这是一棵护寨树,是苗民的图腾,每当逢年过节,大家在树下载歌载舞,在特别重要的日子,树下也成为苗族巴代祭祀的地方。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在《流浪》中写到:“树是那些明了如何向它们倾述,如何聆听它们,了解的人最好的避难所。它们不宣扬学习和戒律,它们生机勃勃地诠释着最古老的特殊的生命法则。”苗族人的树图腾崇拜是一种特殊的生命法则,也是补点人崇尚自然、尊重生命生生不息的轮回。 寨中央有坪名举人广场,碑铭记载着光绪十七年补点书生石国斌中举之事。实难想象,当初的补点大山,树大林密,虎啸山岗,当年艰苦的学子是如何跋山涉水去学堂求学?或者,为了给学堂缴纳束脩,满面风霜的父母为了改变孩子的命运,又是如何将仓里的五谷、圈里的肥猪抬到山外换成一串串铜钱……“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举人广场围栏外的梨花开了一树,在花前伫立良久,而房屋与房屋之间的罅隙传来阵阵呼啸,这声音像风笛,让人清醒。 寨上有人家办白事,如今的乡村很少人会唱丧歌了,寨邻乡亲却全都围坐在一起,追忆着他或者她生前的一切,这也是一种尊重逝者的大礼节。实则在村子的那口老井旁我已然注意到,地上有钱纸焚烧的灰烬,这是村寨的人去世以后一种用瓦钵“取水”的仪式。泪是人间易碎的水,比起乡间其他礼俗,“取水”这一丧葬之俗来得更为庄严肃穆,饱含诸多不舍。 水井是来处,也是去处。 很早前在乡下就听闻有孩子问母亲,“娘,娘,我是从哪里来?”做娘的多半会用指腹按着眉心笑,“娃儿诶,你是我从水井挑来的!”生活在农村,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去,多半与水井相关。出生时,要用井水沐浴;后,井水是喝了一辈子的乳汁;当赤条条地离开这个世界,还要用井水洗最后一把脸,就像洗去俗世里太多的尘埃。在井旁思考,大千世界透明了,你可以看见所有的有关水的脉络,看见了生命在脉络中流动,流向天地自然…… 古井旁的溪沟开满鸢尾花,有一种淡然的香气。 石天银坐在石阶上,长时间不语,仿佛在回忆。二十多年前,他还是村里的一个小伙子,会翻山越岭去寨阳或者矮寨诸多苗圩乡集赶边边场,唱苗族那些缠缠绵绵的情歌,唱他心里那个月亮里的阿妹。他倔强的脸庞曾经洋溢着向往,这是他的青春,被时光蛰伏。 石天银个子不高,偏瘦,脸上缠绕一些我们看不见的风霜,但仍然精神抖擞。他的眉间蹙着,大约蹙着一些心事:今年的春茶能不能掐得出来?那些和候鸟一样南来北往务工的青年男女什么时候回家?还有,今年高考的娃娃能否考取一个好的学校…… 他和补点大约是牢牢捆在一起了。 有人离开这里,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有人留在这里,只为等待自己。石天银属于后者,他说,“以前,补点没通公路,出门便要翻山越岭,许多老人一生都未去过吉首市,我不会离开,我的肩头扛着责任、扛着理想。”“现在,补点不再是‘多补点少补点多少补一点’的补点,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我不敢离开,我的心里还有希望、还有担当。” 假如时光会停滞,山里的日子无非是太阳落了、月亮出来了,谁家的木房子飘起了炊烟;鸡叫了、狗吠了,谁家的男人搬着犁铧去犁田? 补点不一样,她的一年四季的日子是这样打发的:石天银像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他带着乡亲们去河滩抠出一个个矶子岩,修复风化老去的围墙;他带着乡亲们修建恰比河上的跳岩、风雨桥,去河那边的空地打造共享菜园;他带着乡亲们在大山种下黄金茶,给乡亲们的口袋再“补一点”;他还和乡亲们一起制定村规民约,红白喜事随礼不准超过两百元…… 如果说补点是恰比河右岸的原风景,那么,补点一定有这样一个人,从日出到月落,从月落到日出,他在大山画了一大段光阴。这个人是石天银,他成为了恰比河右岸风景里的一部分。 向晚时分,夕阳的余晖洒满恰比河,也落在我们的肩膀,此刻的苗寨像披了一层金光闪闪的外衣。此时,有游人呼儿唤女吆喝回家的声音荡漾在山谷,然后整个峡谷陷入沉寂。石天银站在河岸,显得分外孤独,像是村庄最后的守望。 实际上,我以为自己读懂了补点的孤独,后来我才明白,真正孤独的是住在钢筋丛林里的我们。 (方君才)

标签: 基础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