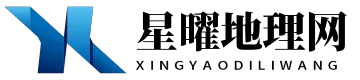这不是一个标签式的“英雄”故事。这是“一个人和他的200多万棵树”。
这更不是单纯的种树、植树、造林,而是一部镌刻着晋北、晋西北人民与恶劣的生存环境作斗争,向风沙宣战的精神史诗。
为了写出心中的将军和将军背后蕴含的精神,鲁顺民在写作时,没有将其塑造得“高高在上”“不接地气”,而是以实地的调研采访、长久的跟踪写作,用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与众不同的叙述结构以及丰盈饱满的细节,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一个有真实温度、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他是时代楷模,但是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样的文学表达,反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艺术感染力,更让读者思考生态环境保护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更让读者深切感受到小切口背后时代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主题。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如今,那昔日连绵的荒山秃岭已经变为林木的海洋,风沙漫天的晋北大地变身绿水逶迤、青山秀丽的生态画卷,每当有风吹过,响彻耳边的是饱满、热烈、沉雄、厚实的阵阵松涛,是散发着人性光辉、人格魅力的将军形象和他的精神在三晋大地的深沉回响。
2024年8月,《将军和他的树》入选“2023年度生态文学推荐书目”。


中国环境报:请您介绍下《将军和他的树》写作、出版的背景?
鲁顺民:2021年底,大象出版社策划一套以“时代楷模”为书写对象的丛书,朋友向出版社推荐,说我可以写一本。张连印将军就在其列。接洽之后,我没有立刻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张将军的英雄事迹被媒体报道得很充分了,再介入,很难有再发掘和发现的余地。
但是到来年春天,我到左云县接触张连印将军,开始采访的时候,想法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因为在此之前,我做过十多年的乡村调查,对乡村几十年的变迁和生存状态有一些了解,尤其是对晋北、晋西北地区,远及毛乌素、库布其沙漠腹地老百姓,与恶劣环境做艰苦卓绝的抗争的历史感同身受。
对他们来说,植树造林不是空洞的宣传动员,而是朴素的生存之道。尤其左云、右玉两县,要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他们对树木和林草的感情,是我们外人无法理解的。他们七十多年坚持植树造林,久久为功,经历过的艰难与探索、欢欣与荣光,也是我们外人很难体味的。这里头,重要的当然是贯穿始终的艰苦奋斗精神,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摸索出一整套种树活树、改善生态环境的科学方法。
第一次见到张连印将军,他已经解甲归田,回乡种树18年。我们会面的地点,就在他最初营造的300亩苗圃里。苗圃内,树木密密匝匝,有200多万棵大小苗木,很成规模。他虽然脱下军装,但30多年军旅生涯,担任部队主官多年,他身上的军人气质仍在。筹划、安排、协调事情,有板有眼,滴水不漏。但坐下来,跟你拉家常,一点点架子都没有。不抽烟,不喝茶,不吃荤,饮酒豪爽,跟日常的农村老汉别无二致。
因为有长期在农村采访的经验,我跟受访对象常常见面熟,没说几句话就会直奔主题,也善于控制和调动受访对象情绪,把握采访节奏,所以很快就跟老将军聊得火热,跟在苗圃里干活的人聊得火热,几天时间,就跟村里人混熟了。
《将军和他的树》这个书名就是在采访过程中确定下来的。我觉得,我此番前来,不仅仅是写模范、楷模、英雄,而是冲着这个人来的。要把这个人写活。
为什么强调“和他的树”呢?树是实指,是指将军和他种下的200多万棵树。还有乡村社会对其的滋养,将军本身就是乡村的一棵大树。树,同时还是结果。采访中间,上高冈,入松林,辛弃疾的词阙《贺新郎·甚矣吾衰矣》常在耳边伴着松涛回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我有信心将这一个人饱满而硕健地呈现给读者,也必须将这个人饱满而硕健地写将出来。所以,我采访时,尽量日常,尽量细微,尽量深入到生活的腠理,而精神提炼与总结,全然不在考虑之列。或者说,精神提炼与总结,已经融入采访全程,只是不见痕迹而已。


中国环境报:植树和“将军植树”,实际已经有同题材作品出版,书写这样一个人物,您是怎样构思的?怎样写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作品?
鲁顺民:我开始采访的时候,已经知道至少有两位作家在写他,其中大同作家马海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已经出版,大约有四五万字。其他的还在写作过程中,或者等待出版,没有见到。马海先生是大同土著,他从老将军4岁丧父、6岁母亲改嫁,然后由爷爷奶奶抚养大写起,一直写到他回乡十多年坚持义务植树的事迹,其中也经过许多曲折与探索,写得比较全面。从他的文章里,大致可以梳理出老将军从一个孤儿到将军,再从将军回乡义务植树的全过程,比较全面,虽侧重于事迹的介绍,但给我形成采访大纲提供了不少帮助。我特别感谢老朋友。
在《将军和他的树》里,当然老将军是主角,还有他的堂弟连茂和连雄,他的表妹和妹夫,他的儿子张晓斌,以及张晓斌的初中同学四旺等,几乎就是一个群体。在我看来,是老将军作为的担当,对改变家乡生存环境的责任心,用实际行动感染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同时,也唤醒了潜藏于庸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才诞生了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群体形象。这个群体形象,才使得“将军回乡植树”显得更加特殊起来、典型起来。
这是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就是写老将军苦难而充满温情的童年,还有他的成长,他的奋斗。他成长的过往,背景是张家场故里的乡里乡亲。少失怙恃,吃百家饭长大。从小学到初中,当第一名,老师和同学的友谊。独自谋生,又有来自叔叔和伯伯们的呵护。外出当兵,当时生产队和公社的干部又对他充满期许。等等诸般,是张连印之所以成为张连印最强大的精神后盾,也因为有这样的少年经历,让老将军对家乡念念不忘,退役之后毅然决然回乡做些事情。谈到老师、同学,谈到乡村干部,老将军每每珠泪洒襟,难以自抑。是乡村教给他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在文本构思的过程中,我没有按照普通传记的写法,从少年平铺直叙一直写到晚年,而是从将军回乡写起,然后有意将两条线交织起来,这是一种近似于小说的构思。两条线互相交织,互相印证,既呈现出张连印从孤儿到将军的成长历程,同时还原出一位具有乡野情怀的朴素的一面。这样,将军回乡义务植树,与其青年成长的过程交互呈现,就具有了相当的象征意味。将军本来就是一棵生长于乡土乡野的大树。他的根在哪里,他精神层面的枝和叶又为什么会如此不同,结构本身就做出了回答。这种结构的好处显而易见,从文本意义上讲,所呈现的主要事迹相对集中,同时又不失历史背景呈现,现场感更加强烈。
报告文学最终是要以文学的形式呈现给读者的,而现场感,是小说等艺术形式的基本要求。如果没有现场感,或者现场感不强烈,文学的意味也将大打折扣。
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既要呈现实实在在的植树绿化,更多的着眼点,还在于将植树绿化这个行为抽象思考。他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么多将军,他回来了?本来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为什么偏偏放着福不享,却要放下钢枪,拿起锄头做回一个农民?他跟普通的父老乡亲们的区别和共同之处又是什么?多关注这些,要比只关注他植树绿化本身对塑造这一个典型人物,显然更重要。

中国环境报:作品中写了很多真实感人的情节细节,是怎么抓到的?又是怎样安排取舍的?
鲁顺民:情节和细节,不独是小说类文学作品逻辑推进的基本元素,也是呈现文学魅力的有机载体。你很难想象一部细节不生动,情节单薄的文学作品可以成立,即便是先锋的、现代的意识流小说、诗歌,即便是在淡化情节的抒情性作品里,没有细节和情节的推动,人物也很难立起来。
就《将军和他的树》而言,那些丰富细节的表达,曲折的情节叙述,无不是对“报告文学”体裁的文学性构思。比如说,张连茂缺了一颗门牙的笑、老支书推开饭碗的叹息、张连印在月夜里因为缺乏资金的失眠,还有张连印直到晚年才搞清楚自己的确切生日等。这些情节和细节,都是采访过程中主人公在庞杂的叙述中偶尔提及的“不重要”内容,在他们看来,是闲话,不是主体内容,但我在整理录音的时候,注意到这些细节和情节,恰恰是表达文学意味,承载人物心理变化的关窍。别人可能不注意,但作为一个作家,这是职业敏感,然后单独抽出来,单独构成小节。果然生动。但不是虚构。
曾有人讲,诗歌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既要清晰地抒情达意,同时还有格律要求。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的孰重孰轻、孰多孰少,把握平衡的过程,而是文体本身的要求。报告文学也一样,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报告文学一方面是报告,一方面是文学,二者之间不是度的问题,而是融合的问题,互为表里。不然,凭什么称报告文学?报告是内容,文学是表达,表达的是内容,报告也在表达。
事实上,有人说书中的情节与细节,是小说式的虚构,也未尝不可。小是什么,不就是一个小心思,一个小动物,一个小特征,一个小纠结吗?丰富的细节与曲折的情节多了,小多了,文学性也就浓郁起来。

中国环境报:将军种的漫山遍野的树怎么样了?将军的树背后,有没有山西人普遍的一些特征,比如“敢栽树、能栽树、会栽树”?
鲁顺民:截至我到访的2022年4月,张连印将军回乡植树第19个年头,共植树绿化20209亩,栽植苗木205万余棵。换算成土地面积,他种下的树,合13.473平方公里,占左云县面积的1%还多。
他2004年种下的头一茬树,都是外调的成苗,成活率不高。后来经过补栽,头一茬林子的树,已经有胳膊粗,蔚为壮观。之后的6000多亩义务植树林,已经绿云浮天,覆盖了几道大梁。最直观的,是张家场村后的东梁和西梁,还有将军台梁,都是竖成列、横成行的大林,是高耸入云的樟子松树。尤其是最初的300亩苗圃基地,几百万棵松树、柏苗密不透风,是左云县十里河滩的重要景观以及右玉干部学院的现场教学点。现在,左云县依托长城一号旅游公路,打造十里河湿地公园,将军的这个苗圃是现成的景观,也给治理十里河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巧的是,左云县与右玉县相邻,走高速也就四五十公里,像张家场这样生态变迁的区域在两县之间并不鲜见。民间组织、县林业部门的基地中,像张连印将军这样规模的基地,两县有十七八处。今天,右玉县林木覆盖率达到51.7%,左云县也不差,达到49.2%。所以,我在书中说,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一直潜藏于民间日常之中,张连印和张连印们,正是唤醒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那个人。
2024年3月,张连印将军去世,灵柩回乡,万人相迎,最后他的骨灰用无人机带着升空,撒在他生前种植的万亩树林里。

中国环境报:山西文学界是重视生态文学的,但当前山西缺乏生态文学重头之作。您对此怎么看?您在生态文学创作方面有何打算和计划?
鲁顺民:如果把生态文学作为一个泛化的概念,在国际上也不过百年历史,经典的作品有《瓦尔登湖》《沙乡年鉴》《一平方英寸的寂静》。至于今天的生态文学,日益受到公众的关注、追随,既与今天生态文明建设倡导有关系,也与公众的生态观念逐步形成有关系。生态文明,是未来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词之一,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至于山西的报告文学,或者非虚构文学在全国引发关注,原因在于我们有一支强劲的创作队伍,比如哲夫、赵树义、蒋殊、宋耀珍等,有许许多多值得书写的生态故事,比如吕梁山在黄河悬崖绝壁上植树成功的范例、壶关县在太行山严重缺水山区阳坡植树成功的范例、偏关县专业造林队伍屡创奇迹的范例,以及陵川县结合文旅以三产养生态以生态促三产的范例……范例甚多,值得书写,精神可嘉,应予弘扬。这些,都是我们作家应该关注的。
《将军和他的树》获得关注,是我没有想到的。此后如有恰当的选题,我会毫不犹豫投入其中。
张连印们遍及吕梁,魂漫太行,精神不死永生。

个人简介
鲁顺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山西文学》主编。著有《天下农人》《礼失求诸野》(合著)《山西古渡口——黄河的另一种陈述》《送84位烈士回家》《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合著)《将军和他的树》《潘家铮传》等。获得赵树理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徐迟报告文学奖提名奖等多种奖项。